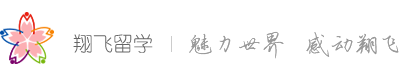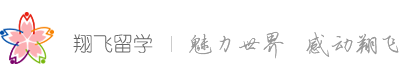我回想起那日,那是留在日本的最后一夜,我跟薇薇酱从book-off满载而回,我们两个瘦小的身影,一边拖着装满日漫的沉重的小破行李箱,一边神经病似的嚷嚷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理直气壮地走在几乎无人的夜晚道路上。
即将走到车站外的升降梯时,一个胖大叔回头看了我们两个一眼,道:“哎哎,两个小丫头,别吓着人家日本人了。”我跟薇薇酱略微一愣,相视着“噗呲”笑出声来,紧跟着胖大叔一起走进了电梯。
胖大叔扫视了我俩一眼,问道:“你们哪个学校来的?”
“暨南大学。”
与胖大叔同行的瘦高个马上从笔挺的西装里拉出来一根橙黄橙黄的带子。我跟薇薇酱眼睛一亮,乐开了花:“也是翔飞的!”“嘻嘻,我们被认出来了呢。”
那一夜并不算太冷,两个瘦小的身影就轮流把笨重的行李箱抬上过街天桥、一遍又一遍的石阶,一人一半的路程。有伙伴分担、分享,是件快乐的事,一个人的时候即使身处热闹的新宿大街,也会觉得内心安静得好寂寞。有时我也会享受一下这样安静病态的寂寞,一个人发呆思考,觉得就这样不被察觉地成长起来了一样,多数的时候还是期待伙伴的。
日本的城市就是这样,即使满眼的热闹都会让你觉得安静冷清到灵魂出窍,直到身边伙伴的轻声呼唤把你拉回三次元人间。后面我才慢慢意识到,那是因为在街道上在那么些热闹的商店集市车站,没有人大声喧哗,间隔传来几声店里服务员的彼此呼喊、电车里略微震耳的广播,更是让城市凸显平静。话说我在广州的地铁上经常因为身边喧闹鼎沸的人声而听不清广播的声音,想想自己习惯了那种喧哗的热闹之后,难怪会在这里尤为觉得寂寞呢。
最后一日白天的时候,我一个人去了浅草寺,坐上了不是高峰期的地下铁,车厢里人烟稀少,扶手有规律地摇摆着,晃得我只想睡觉。于是我便真的安心地睡过去了。醒来时恰好在浅草站前一站,下了车,一个人默默地沿着指示牌走在浅草寺附近的街道上,旁边的街道不像寺内那么火热,有种静悄悄的冷。天湛蓝得可怕,在原宿附近等车的时候是,这里也是,蓝的像小时候不小心涂多了颜料的画儿。
我路过涛哥说的那条,卖着和服配饰的小街,天空开始下着轻飘飘的细雨,并不足以打湿衣衫,但是这条小街还是好冷清。有一家卖各式小玩意的商店,店长大叔一本正经地蹲在门前摆弄商品,把小商品跟和菓子摆放的整整齐齐的。
“明明就没有什么客人路过呢。”我心里这样想着,看见大叔认真的劲头,很想帮忙买一盒,但是兜里剩下的日元不多,便又叹一口作罢了。
沿着外围慢慢走,还遇见了拉着类似黄包车的年轻男子,有客人来,非常热情地招呼着,帮客人拍照,给客人围上防寒的毯子,拉着客人沿街解说一些古旧的建筑,有说日语的客人,也有不说日语的客人。再往前走便遇到穿得像炮筒子的女人们,在招呼客人进自家的居酒屋取暖,那些居酒屋的座椅都基本摆到了店外面,用北方冬天常见的塑料门帘围起来,遮风挡雨,简易又实用得很。
我漫无目的地散步着,一点儿也不担心会丢失了方向,走着走着就离雷门很远了,看见整体风格是黑色的浅草站,刚好地面上的东武铁道,有个挺明显的咨询屋,可以允许使用各种语言咨询,我问了去秋叶原的换乘方法,不费劲就去了秋叶原,都懒得自己去查手机地图。
其实去到电器街之后,我只是站在路边发呆,根本没有去一开始兴冲冲想要去的女仆餐厅,看着漂亮妹纸们cos的女仆装,突然觉得一个人进去非常不好意思呢,还是留到下次跟朋友一起去吧。然后便一头扎进book-off,差点被吞噬在里面,后面遇到薇薇酱才俩人一起归去。
我们从关西一路到关东,有热乎乎让人想扔掉外套的大晴天,也有雨雪交加的阴霾天,仿佛四季随机交替上演,尤其是在京都上课的那一小段日子。我是特别容易晕车的人,所以在车上的时间,我基本是荒废的,来不及去看车外匆匆的风景,偶尔抬头只看到那蓝进骨子里的天空,飘着比我在内蒙、在鸭绿江、在Hongkong看到的还要大朵的白云,并没有什么特殊形状,就那样优哉游哉地飘着,像我一样漫无目的在天空散步,或者是遇到淅淅沥沥的雨珠,模糊了整个车窗,呵气擦干一块,也还可以看见窗外的海,平静无澜的灰色却并不令人感到压抑,会让人想起一只猫,一杯热茶,仅此而已。
京都也许是我第二喜欢的日本城市罢,所有的房屋都低矮低矮的,于是很容易便暴露出大片大片的天空。当你走在校道上,那些翠绿的树,云杉啊松树啊之类的吧,在蓝天红砖的映衬下,我突然明白过来什么叫“苍劲”。它们像卫士一样矗立在那里,即使是雨夹雪的天气里,也几乎巍然不动,让我一度以为它们是塑胶铸成的。其实在日本的时候很少看到假花假草,那日温泉旅馆的自助餐里,我们几个人傻乎乎的讨论为什么旅馆要把假花泡在水瓶子里呢,然后每个人轮番抚摸验证之后发现那朵寂寞又鲜艳的针瓣花是真品。
在同志社的校道上,每隔几步还能看见穿着帅气靛青色制服的保安爷爷们,头发有些许花白,眼睛里却神采奕奕的。我当时好奇:“为什么他们不去染发呢?那样就变成帅大叔了呢。”在快要走出同志社的小门时,我看到了新岛襄先生题字的一句话,心中为之一动便停住脚步拍下来了,那句话的意思便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瞬间感谢自己,高中时有好好念语文,也感谢中文的博大深远。
在同志社大学小门出去,走过150米的小道便可以到达相国寺,没有供奉着什么特殊的神明,故也没有看到任何人前来参拜。里面也尽是些苍井的松树,跟日本神社、寺庙里随处可见的碎石子路。因为时光还很早,附近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相国寺里晨跑,几个温柔的老师分别守在一个四方绿化带的拐角处,给奔跑着的小朋友们加油鼓劲,戴着红色或黄色防晒帽子的小朋友们,有的认真地奔跑着,防晒帽的耳朵都飞了起来,有的喘着气想要偷懒,却还是在老师期待的注视下亦步亦趋地跑完了。老师之中有一个笑眯眯的老太太,轻声唤着每个路过她的小朋友的名字,有个小女孩冲到她面前撒起娇来,她低声说了句什么,小女孩又欢快地向前飞奔而去了。
我数着时间往前走,听着头顶上路过的乌鸦,它们随处可见,几乎在后面去到的每个大学、寺庙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踪影,它们也是淡淡地飞过,不会去打扰路人,性情跟这里的人民一样,所以才会被喜爱吧。走近相国寺的艺术博物馆,理所当然的没有开门迎宾,我误入了一个小院,看见工人在院子里俯身修剪着花枝,我就那样站着看了他们一小会儿, 他们居然认真得谁都没有发现我的存在,头也不抬地盯着手上的枝叶,偶尔闲聊几句。
在同志社上课的那几天,我几乎没有在外面用餐过,我喜欢坐在食堂里听着动漫里才会听到的聊天声,好像有好多天然的声优聚在旁边,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日,坐下来吃拉面的时候,身旁有个顶着卷发的学生喊了声“群马君,你要去哪?(けんまくん、どっこいくの?)”,大概是这样吧,我抬眼看他,他也刚巧低头对上了我,带着略微抱歉的微笑冲我点点头,圆脸上露出害羞的小酒窝,我心里响起一声“咯噔”,那天的用餐点数还跟食堂推荐的每日营养点数一致,被涛哥“请客报销”了餐费呢。就这样的羞涩的微笑,才会让人心动不已、喜欢不已吧。
上课那几天,因为晕车,我一直昏昏沉沉的,时而能积极响应老师的提问,时而跟不上老师们的进度。现在已经想不起教授们的名字了,外国人的名字好长呢,但是他们的脸跟课程还是印在了脑子里,心里还残留着对他们的敬意。
课程结束之后的日子,涛哥跟皮卡丘小姐姐带我们去了袛园跟大阪心斋桥。跟伙伴们走散后,我自己走在黑漆漆也灯火热闹的袛园街上,走在人来人往飘雪的心斋桥大街,遇见了艺妓、走进隐于街市的日料小店、凑当地人的热闹买了酥香可口的牛角包、沉迷于药妆店买买买、撞见白天是饭馆晚上是牛郎小酒店的店铺,但这些新奇的兴奋感最后回想起来,还是打不过独自一人的寂寞。我在想:那些独自一人生活的留学生或者当地大学生,他们打工、上课,遇到悲伤的时候是怎么处理伤口的呢?
直到很后面我们抵达东京之后,直到跟着伙伴们一起去寻找失物、游荡街头,直到做足攻略的伙伴领着我在台场横冲直撞,直到大家一起为毕业典礼排练节目,我才学会别人一开始就轻易拥有的东西。
一直有伙伴陪伴的同学们,回想起这十来天在日的经历,肯定满满的都是欢喜、兴奋跟不舍吧。我却在这里学会了平静跟想办法让自己适应别人,适应别人才能快速地找到伙伴,在中国的时候从来不觉得自己一个人活下去会有什么问题,来到这里我才知道,想要一个人活下去是要多坚强才能做到,也更好让我重新审视、珍惜身边的友人;在这里我被很多人都温柔对待,那些刻进脑子里的温柔让我知道,生活能力比学习能力重要得多。
晚饭的时候,我对妈妈说:我还想再去日本呐~即便是没有能力去留学,也还想再一次被那样温柔的对待,还有想看的风景跟人在。
以上便是翔飞这个集体带给我感动,没有大义,看似寂寞,却会伴随我一生,这是我跟随旅行团或者自己跟着攻略自助游都无法获得的,一辈子的生活技能与热血回忆。我会努力,想要再一次遇见那群从一开始就温柔待我的翔飞的人们。
(供稿:潘雪君)